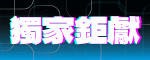當ChatGPT能在幾秒鐘內產出一篇文章,當AI的生成能力日益精進,你是否也曾思考:我還能做什麼?本文主要探討AI時代下,創作者的價值為何,並提供實用建議供有AI焦慮症的人參考。
面對 AI,這個時代還需要創作者嗎? 這篇來自 Manny YH Li 點餐,回應最新一集曼報《(自)媒體的 AI 焦慮指南》。
同時也是整理我目前對「AI 會取代創作者嗎?」這問題的所有想法。你不需要聽過這集曼報,也完全可以看得懂這篇文章。
這一集真的很過癮,除了 IEO 跟中傑在嗆曼尼的部分很精彩以外,兩位來賓也對「創作者的價值」提出很好的洞見。
我對這集的整理是,「創作者的價值」有四種:
1. 工具價值:偷懶的紅利,創作者會幫你找資料,節省時間。
2. 觀點價值:創作者會提出嶄新的觀點,問出沒有人問過的問題。
3. 策展價值:創作者可以找到稀缺內容,用最精準有力的方式呈現
4. 情感價值&信任感:創作者會與受眾建立真實連結。
雖然節目中的討論比較偏向「因為有這四大價值,所以創作者不容易被 AI 取代」,但我的看法是: 其實可以被取代的 。
這四大價值都有可以被 AI 取代的地方,但不是那種零或一的完全取代,而是時間快慢跟程度的問題。
例如,「工具價值」取代速度最快也最徹底,再來是觀點與策展,「情感價值」最慢也最淺,但仍然會被 AI 取代。
這聽起來很可怕,但我認為這其實是好事。
因為這代表人類終於從「創作的勞動」中解放,踏入「無用之用」的領域,產出更 real 的內容。
所以這篇文,我想站在兩位來賓的肩膀上,延伸討論「創作者的四大價值怎樣被 AI 取代」、什麼是「無用之用」,以及「 2025 年,我對創作者 AI 焦慮的六個建議」。
文章目錄(點擊即可前往該段落)
- 「工具價值」是最脆弱的護城河
- 「觀點價值」只是一種表象,沒有人在意創新
- 「策展價值」:這個時代需要策展人
- 「策展價值」(二):AI 可以取代策展嗎?
- 「情感價值」:人類是部落動物
- 人類的主戰場,在「不完美」。
- 死死盯著自由看。
- 2025 年,我對創作者 AI 焦慮的六個建議
1.「工具價值」是最脆弱的護城河
創作者的「工具價值」就是:我周加恩幫你找好資料,這樣你不用再去問 AI,省下你自己搜尋的時間。
這也是過去媒體/自媒體的主要推動引擎:「偷懶的紅利」。
節目中,中傑的論點是:「過去的搜尋工具越來越先進,人類還是一樣懶惰,所以在 AI 時代人類還是一樣需要媒體。」
啊,我覺得這很有討論空間。
因為 AI 本質上不是 Tool 而是 Agent——「會使用工具的工具人」,跟過去搜尋引擎只是 Tool ,有本質上的不同。
雖然現在的 Perplexity 還鳥鳥的,但大致上可以確定會往「個人化」跟「零幻覺」的方向發展。
個人化沒有什麼難的,零幻覺(zero-hallucination)雖然有爭議,但大致上可以看出來當語言模型越大,幻覺就越低。有研究認為 2027 年就會達成。
也就是說,在最快的情況下,創作者的「工具價值」在兩年內就會被 Perplexity 完全取代。我覺得這不是太大的威脅,因為創作者本來就應該把資料找好之後,再來說故事。
唯一要擔心的是那些「我的價值只是幫你找資料」的創作者,例如單純整理新聞、整理旅遊資訊的部落客/電子報。
尤其如果商業模式又只是「在網頁裡放廣告,用流量變現」的,那可能會受到很大的衝擊。但這類創作者本來就沒賺很多錢了,所以其實有沒有 AI 沒有太大的差別。
好,所以「工具價值」兩年內就會被取代,但不擔心,因為創作者更重要的價值應該是另外三個「觀點、策展、情感」。
我們繼續來聊 AI 怎樣取代這三件事。
2.「觀點價值」只是一種表象,沒有人在意創新
「觀點價值」的意義是:曼尼 Angela 會提出你沒有想過的觀點跟切角,因此聽曼報很爽。
許多人會從這點延伸:創作者的價值,就是提出沒有人問過的問題——提出嶄新的觀點。但我覺得這是假的。我覺得「觀點價值」只是表象,創作者的價值不是「提出新觀點」。
一來是,「提出新觀點」是 AI 擅長的領域。我個人使用《 AI 前輩 》這個提詞,產出過 N 個新點子;大部分時間根本不需要刻意下提詞,只要單純對話,讓 AI Review 我的想法,就會有新點子出現。
甚至學術上,AI 的創新能力也受到初步認證了。德國的普朗克光學實驗室拿 5800 萬份學術論文訓練成「專門產生研究題目」的語言模型 SciMuse,產出的題目有 25% 是「可用」,10% 是「非常有趣」。
結論:別跟 AI 比創新,人類比不過。此外,不管有沒有 AI,創作者的工作從來就不是創新,而是「服務」。
我舉個例子,我在剛開始講喜劇的時候,曾經有過一段低潮期。
我發現幾乎不管我寫什麼笑話,我都可以在英文世界找到幾乎一模一樣的切角、觀點。——任何我寫出來的笑話,都已經被寫過了。
我挫折到在台上跟觀眾說這點,抱怨完,有個觀眾悠悠地回我:「可是我們沒有聽你說過啊。」
這位觀眾可是真知灼見。
受眾根本不在乎創作者是否「創新」。受眾只在意創作者有沒有「服務到我」。受眾真正在意的是,創作者有沒有說出那些「我想說但說不出來,我想要『想』但想不到」的事情。
在喜劇產業裡這點早就是普遍事實了:所有的笑話早就被寫完了,但這完全沒差。因為喜劇演員的工作不是探勘語言邊界,而是「說出觀眾自己想講,但是講不出口」的話。
在認真分析的內容也是一樣。我聽曼報,不是因為 Angela 跟 Manny 的觀點超級無敵創新,而是因為他們會用「我喜歡的觀點」切入複雜現象。如果我真的想要創新,我應該去讀學術論文,不是曼報。
創作者的「觀點價值」只是表象,表面上好像創作者提供了新的觀點,但其實本質上還是在服務受眾,給出那些「我想要『想到』的觀點,但是我沒有這樣想過,讓創作者幫我想出來。」
因此拆解下來,我認為「觀點價值」核心還是「策展價值」。所以我們接續下一點。
Now we're talking.
3. 「策展價值」:這個時代需要策展人
到底什麼叫「策展」?
策展,就是創作者去找資料、挑選、排列組合,賦予自己的獨特意義,呈現給受眾看。
策展=洞察+品味+設計+說故事。
創作者本質上都是「策展人」。
節目中有一個金句,叫做:「Curator 比 Reporter 重要」雖然有點激進,但這句話我非常認同。
注:「Curator 比 Reporter 重要」,這句話有點過頭了。Reporter/開採資料人/基礎學科研究者當然也重要。這本質是社會分工的問題。
家母是做峇里島甘美朗音樂研究的民族音樂學者。我家的書房累積了大量的錄音帶、錄影帶,都是她親自去印尼N趟田野調查、認識老樂師,幫他們錄影累積下來的資料。可是,如果沒有人整理這些資料重新策展,我直接上傳到臉書上,有人會去聽嗎?幾乎不會。
這是目前「傳統音樂研究」在面對的問題:沒有人在乎。為什麼沒有人在乎?因為只有 Reporter 在開採資料,缺乏 Curator 把傳統音樂的美感呈現到大眾視野裡。許多領域都在面臨同樣的問題,不論有沒有 AI,我們永遠都需要策展人。
Curator 比 Reporter 重要,撿回收的比挖礦的重要,那些把資料重新整理呈現在大眾面前的人,比開採資料的人重要。
我想到兩個例子。第一個例子是最近錫蘭的《你的身心靈不需要課程》。
他做的事情,本質上就是把學者 Margaret Singer、John Hunter 的思想重新詮釋,套用在台灣的脈絡裡面,推動成效好到連 Hunter 本人都讚賞。
如果沒有錫蘭這位 Curator 來做這件事,學術研究不可能進入大眾視野裡面。
這就是那個哲學問題:一棵樹在無人島倒下來,沒有人聽見,它真的有倒下來嗎?如果某個學術研究可以拯救世界,但沒有人知道它的存在,那有意義嗎?
這是創作者的重要社會功能——對於大眾在焦慮的大部分問題,答案已經存在了,但是社會需要策展人把答案呈現在大眾面前。
社會需要創作者來「找答案」。
第二個例子,是關於「策展」可以有多強的力道。
我第一次被「策展」的力道真正打擊到,是在阿姆斯特丹的熱帶博物館。
一般我們想像的博物館,就是擺設很多東西,這個是恐龍,那是三葉蟲,這是他的介紹,下面是 4D 體驗....逛完了,買紀念品。
但荷蘭人身為策展大國,從 17 世紀就開始搜刮世界各地的東西給歐洲人看,他們在「策展」這件事真的有深厚底蘊。
「熱帶博物館」一樓有個常設展,但比較特別的是:他們的展覽不是用「主題」分類,而是用「問題」。
例如,有一個展區,策展人提出的問題是:「什麼時候,我們真的在『家』?」
然後展區給你看一小段紀錄片,關於在美國加州、德州的墨西哥移民,閒暇時會玩一種很特殊的手球運動(Pelota Mixteca),規則類似排球,兩邊隊伍要盡可能不讓球落地。
打擊者會帶著類似棒球手套的東西來打這顆球,上面有墨西哥風格的華麗裝飾。美國很難買到這種手套,他們為了打這個傳統手球,不斷拜託回家鄉的人帶手套來美國。
受訪者:「當我們在打這個球,我好像忘記我在美國,又回到墨西哥一樣。」這個展覽重點是激發你思考:「什麼時候,你真的在『家』?」
從墨西哥手球的故事你會發現,「家」不一定是物理/地理空間的,家甚至不一定是跟特定那一群人——「家」甚至可以是一個「運動」。
我整個人被勾進去,尤其對我這個剛漂泊到異鄉的移民,這問句直接刺穿我的心臟。我坐在展區前面沉思了半小時,完全無法停止思考。
我覺得這是「策展的功力」: 精準辨認受眾心裡最焦慮的問題切角,並且找到非常獨特觀點的材料來「說故事」,激發你重新看這個世界。
在衝突、破裂、死結、矛盾、複雜之間,找到新的切角,讓你重新思考「標準答案」以外的可能。
這個社會需要策展人。這個社會需要創作者來「找視角」。
結合「找答案、找視角、說故事」這幾點,有效的「策展」對社會是具有治癒功能的。
美國小說家 Toni Morrison 說過一段話我非常喜歡:「This is precisely the time when artists go to work. There is no time for despair, no place for self-pity, no need for silence, no room for fear. We speak, we write, we do language. That is how civilizations heal.」
在人類自我認同即將破碎動盪,焦慮海嘯即將來臨的 AI 時代,沒有任何時代比現在更需要創作者,需要策展人。
4. 「策展價值」(二):AI 可以取代策展嗎?
短期內我覺得很難,至少五年內不會。在短期內,人類策展人面對 AI 有三個主要的護城河:
(一)「共情能力」
回到:策展=洞察+品味+設計+說故事。
「洞察」的部分, AI 大數據辨認受眾痛點的精準度,已經超越人類了,也已經落地應用得很成熟了,看看手機怎樣監聽我們。
但是在後續「品味、設計、說故事」這段,目前都還有很大的 gap 要彌補。後面這段產線非常吃「共情能力」,這點短期內我不認為機器可以滲透到人性的這塊。
(二)「真實經驗」
AI 最大的缺點就是它不是人,AI 不能有真實經驗。
這點尤其 favor 那些有領域實戰經驗的創作者,例如你可能有創業失敗十次的經驗,那就你產出創業相關的內容就很有說服力,因為你踩過無數個坑。
AI 只能模擬「一個有真實經驗的人」,但不能真的有真實經驗。你具備越多實戰經驗,你作為創作者的說服力就越強,能創造的情感連結跟信任感就越強。
這是為何 AI 再強,曼尼、IEO 這樣的自媒體都不會被取代,因為是真實的人,分享真實的經驗。
(三)「人脈網絡」
AI 不是人,AI 不能交朋友。
中傑講到一個很好的案例:AI 可以分析一間公司財報、新聞、資訊怎樣,做到大概五六成,但是 AI 不可能直接去訪問公司的創辦人本身想法。
其實,一般阿貓阿狗也不能直接去訪問到公司經理人本身。所以還是回歸到最核心的邏輯:「網絡效應是最難被攻破的護城河」,不論對人或對 AI 都是。
對於大公司產品來說,網絡效應是使用者生態系;對個人創作者來說,是個人的人脈網絡。
例如 Acquire 訪問到張忠謀,人脈網絡可以讓你產出超級稀缺的內容——本質上還是真實經驗,大佬的真實經驗。
這三個護城河裡面,「共情能力」是最弱的護城河,我瞎猜測可能三五年後 AI 就可以「超懂你」了,然後會出現大量的落地應用。(例如:不會 burn out 的心理諮商師)
但後面兩個護城河:「真實經驗、人脈網絡」是目前我認為 AI 怎樣都不會攻破的點。
因為這種「分享自己/他人的真實經驗」,本質上都是在「Tribe,部落」的層面上運行,你在做的事情跟五千年前智人在營火旁八卦,基本上是一樣的。
如果有一件事已經存在五千年,那你基本上可以假定它繼續存在五千年。所以我們來到最後一點:Tribe。
5. 「情感價值」:人類是部落動物
哈拉瑞在《 Nexus 》中說的:「資訊不是設計來傳遞真相的;資訊真正的功能是建立連結,塑造團體。」
你當然可以說:創作者提供了很多工具價值、觀點價值、策展價值,但是當你拆到最底層,說穿了,我們都是來「交朋友」的。
不管你是商業分析還是喜劇演員,都一樣。
AI 並沒有改變創作者的底層邏輯,AI 只是把表面那些價值給全部拆了,逼迫我們面對這件事:只有很少人會追求真相,大部分人們真正在意的不是事情的真假對錯,人類在意的是「我們是朋友」。
部落。
部落是最後一條護城河。我現在就可以訓練出一個 MannyLM、IEOLM、商周LM,各種數位影分身之術。
但這怎樣都不會取代掉本尊,因為受眾不想跟機器交朋友,我們想要跟人類交朋友。
人類是部落動物,我們天生喜歡追隨領導者。
在商業領域裡,我們追隨「分析的 Leader」;在喜劇領域裡,我們追隨「幹話的 Leader」。不同領域,同樣的部落邏輯。
如果我們針對這點來思考「AI 會不會取代情感價值,成為讓人類去追隨的機械 Leader?」
哇,那會非常科幻了。仔細想想,真的不可能嗎?我也覺得完全有可能。
只要 AI 發展出精準的共情能力,成為 Leader 就易如反掌了。
現在的 AI 已經有表象的「假共情」了,例如:已經有脆文說 GPT 比男友好聊。或者,你知道有個東西叫 Rizz GPT,專門幫你回 Tinder 訊息,評價裡一堆人說他靠這個成功把妹嗎?這根本還只是用幾個提詞寫出來的東西,沒有任何深度工程成分。
現在「虛擬偶像」還是很小眾的嗜好,我覺得那是因為虛擬偶像還「很假」。等到你無法區分出虛擬偶像跟真實偶像的差別時,那就很精彩了。
我們馬上會進入《雲端情人》的情境:「人能不能喜歡機器,追隨機器,甚至愛上機器?」
當然可以。
人類的共情能力充滿不穩定,機器只要搞定這點,人類一點競爭優勢也沒有。
加上 VR 、腦機介面...用機器做出一個完美的創作者、KOL、情人,完全可能啊。
最終,我覺得這是很像「經驗機器」的哲學問題:如果把你的大腦放到一個機器裡,你會進入一個超完美的虛擬世界,所有你想要的一切都可以獲得——爬上聖母峰、成為億萬富豪,一切。
但同時你會知道,這一切都是假的。
你願意進入這個機器嗎?
這是哲學家 Robert Nozick 提出的,本質上是一種價值選擇的問題:面對人生,你要選擇那些「虛假的完美」,還是「殘缺的真實」?
我的直覺答案是「選擇真實」,我不想要被欺騙的感覺;但是我在高中、大學都問過同學這個問題,我得到很多「當然進入機器啊」的答案。
加上現在奶頭樂、短影音的現象,我覺得會有一部分人,寧願選擇虛擬的美好,也不要真實的殘缺。
所以我發現這很可能會變成兩種「內容消費」的習慣:一派人就喜歡超完美,把你服務得服服貼貼的「機器內容」;另一派喜歡有點不完美,但很真實的「愛心手工內容」。
所以我覺得不是完全取代,而是讓「虛擬偶像」地位跟定義都擴大,成為一個新的競爭者類別。
那對個人創作者來說,其實也不是什麼大問題,就是像過去十年傳統媒體多了自媒體競爭者一樣:沒有被取代,只是進入下一個均衡。
6. 人類的主戰場,在「不完美」。
AI 普及之後,我注意到一個感覺是:人們開始有點厭倦了「很完美」的東西。
尤其在英文內容市場,我注意到人們會刻意用 typo 、多一點幹話甚至刻意留下贅句,來顯示這是真人產出的內容。
我覺得,這太棒了。
人們終於開始理解「無用」的價值了。
大概是 2024 年初,有段時間我忽然開始 AI 焦慮,覺得 AI 一定有一天會寫出超強笑話,取代喜劇演員。怎麼辦?
然後,我去看了高雄開港喜劇俱樂部,主辦人阿海的專場。
阿海自己也是喜劇演員,但他敢辦專場真的是非常勇敢,甚至太過於勇敢的一件事。因為,他的笑話,早就在 open mic (平時的測試練習場地)裡面講過 N 次了。所有他的粉絲,包含我,都聽過 N 次了,我們連 punchline 都記下來了。
你猜,他要辦個人的一小時專場,是誰會來買票?當然是我們這群粉絲。
在這個情況下,他敢辦專場我已經超佩服他的勇氣了。偏偏,他記性又不是很好,或者是那個時期真的太忙了...專場當天,他在台上瘋狂忘詞。
哪有人辦自己的專場,自己不記得段子,然後觀眾比你還熟悉段子的啦!
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?一開始是阿海的女朋友在旁邊幫忙提詞,後來觀眾們放棄裝了開始喊出他的 punchline,到最後阿海也放棄背稿了,他直接在台上講笑話的上半段,下半段讓觀眾幫他講完。
我們一整群人,觀眾加演員,一起完成了這場專場。
我這輩子永遠忘不了這場演出。
那個社群感、連結感、荒謬感,一切完美地剛剛好到位,完美抓到「我就爛」的喜劇精神,永遠無法複製的一場專場。
即便我現在在美國看過世界一流的喜劇演員,這場阿海個人專場,仍然是我這輩子最愛的一場喜劇演出——沒有任何一個刻意安排的表演可以做出那天晚上的經驗。
看完表演,我走出場地,心中只有一個感想:我找到 AI 永遠無法取代人類的地方了。
AI 永遠做不到「我就爛」;AI 永遠做不到「無用;AI 永遠掌握不到「無用之用」。
而喜劇舞台的邏輯是這樣的:你越是完美,你就越討人厭。你的缺陷越鮮明,觀眾跟你距離越近,你更容易跟觀眾建立連結——情感價值。
喜劇演員是最理解「無用之用」,最擅長利用「不完美」的族群。
如此擅長,美國站立喜劇有九億美金的市場規模,都建立在「缺陷」上。
我對 AI 的看法是,它最終一定可以做到所有「完美」的事情,我上述說的護城河,甚至包括真實經驗,如果哪天全部被拆了,我也不會意外。
但是對於「不完美」, AI 大概取代不了吧。萬一真的有一天,AI 也出現了「不完美」跟「缺陷」,那就真的非常可怕了。
那代表人類真的打造出了矽基文明,我們得要開始思考機器的權利和倫理。
但這就扯遠了。
我們聊點比較務實的:現在的創作者,可以怎樣面對 AI 焦慮?
7. 死死盯著自由看
過去這兩週,真的是我最充滿 AI 焦慮的兩週。
主因是,我最近收了一個寫作學生,她只用兩週的時間用 AI 寫作,就寫出了一篇爆文。
接下來,她的產出水平,直接達到我苦練一年半的水準。
沒有任何 AI Agent design,沒有 n8n,沒有 o1 推理模型,甚至沒有提詞工程,就是單純 ChatGPT 的對話。
你說,我該怎麼混?
這個焦慮,本質上也不是那種「我要失業了」的生存焦慮。反正大不了內容做不下去,我就在美國賣牛肉麵嘛。每次技術革新都有大量的新機會,不可能真的失業。
這個 AI 焦慮本質上更接近是「身份認同」的焦慮:靠,我的學生練個兩週就能寫爆文,那要我幹嘛?
我想到 19 世紀攝影術發明,讓一大批畫師失業的故事。
1839 年法國版畫師莫里塞畫了一幅《達蓋爾攝影狂熱》(La Daguerreotypomanie),描寫了當時銀版攝影術之後,大眾是怎樣狂熱地排隊,每個人爭相拍上一張照。
攝影術發明後,人人都可以在鏡頭前呈現自己的身份。要知道,在這之前,獲得一張「自己的畫像」可是只有上流階級跟貴族的特權。
畫家莫里塞除了描寫當時大眾的狂熱以外,你可以發現旁邊還有幾個絞刑架,上面牌子寫:「絞刑架,供雕刻師租用」。
你可以想像當時的畫匠們何等焦慮。他們的身份認同,被攝影術無情地奪走了,這世界再也不需要畫匠、版畫師了。
如同今天,創作者的身份被 Sam Altman 無情地奪走了一樣。這世界似乎再也不需要創作者了。
可真的是這樣嗎?
因為攝影術的衝擊,這群被取代的畫匠、版畫師,被逼迫著思考:「我拿著這隻畫筆,究竟有何用?」
後續有一小段時間,寫實派繼續苟延殘喘,想要畫出比攝影術更細緻的畫像。直到 1850 年,人類終於發現打不過機器,畫家必須走向別條路。
第一個出現的是「印象派」,如莫內、雷諾瓦等人,他們提出的思想是:
「如果畫面已經可以被機器捕捉,那繪畫該去探索人眼的感受而不是客觀現實。」
從這裡開始,繪畫者不再是「紀錄畫面」的人,而是成為「反思自己究竟看見什麼」的人——他們從畫匠,變成了畫家。
在印象派確立了這點之後,畫家們才開始更大膽地解構現實,於是有後印象派的梵谷、立體派的畢卡索等。
攝影消滅了「繪畫」,但「繪畫」也重生了。攝影術的發明,同時是人類反思自己「如何看見」的時代開始。
同樣的,AI 正在消滅創作,但我很確信「創作」也會迎來一波重生,是人類重新反思自己「如何說話」的時代。
我們都如同莫里塞版畫中的畫師一樣,正被逼迫著思考:「我手敲著鍵盤,究竟有何用?」
舊的身份認同被拆毀了,我們真正在害怕的不是生存與否,而是「自由」。我們必須重新定義自己:
「這一次我是誰?」
「我真正想做的是什麼?」
「我要怎樣做這件事?」
這些問題都很難。但我想邀請你,死死盯著自由看。因為在這個自由背後,是豐饒。
每次變革,都帶來大量的機會。這次 AI 技術變革之大,我無法想像未來十年的機會有多盛大。
同時在這 自由的背後,也是動盪、破碎與焦慮。未來會是充滿困惑與混沌的社會,我們前所未有地需要創作者,需要策展人。
這不是絕望的時刻,不是自憐的時刻,不是沈默或恐懼的時刻。我們必須說話,必須寫作,我們必須說故事。
這是創作者的社會使命。
我想引用 Dylan Thomas 的詩:
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,
Old age should burn and rave at close of day;
Rage,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.
8.「 2025 年,我對創作者 AI 焦慮的六個建議」
《曼報》節目尾聲,曼尼問 IEO 和中傑:「如果今天有個創作者人走進來,說他現在好 AI 焦慮,你會怎樣回他?」
兩位來賓的想法大致上一樣,就是「只做你有興趣的事,如果內容創作沒有興趣支撐,只是想要賺錢,那勸退不要做」。
我也完全同意。能賺錢的方法多得是,不要只為了賺錢而搞內容創作。
但我覺得這個回答不夠充分,實際情況是就算是從興趣出發,大部分的內容創作者還是想要賺錢的。
所以我覺得必須讓這個假想的創作者問第二題:
「加恩,我就是想要兼顧興趣又賺錢,站著把錢給掙了,你會給什麼建議?」
這個問題,我會從六個角度來思考:
1. 策展
創作者的核心價值永遠是策展,你想要回答什麼問題?你想要探索什麼材料?你想要服務哪一群人?這些問題會引導你產出精準、有力的內容,也會引導你打造出受眾需要的產品,不論是 infoproduct、工具還是服務。
一個關鍵是:這些問題不是空想就能解決的,你需要不斷操作迭代,從實作經驗知道「自己真正想回答誰、想服務哪一群人」。
所以思考策展相關的問題,其實不是未來式的思考,而是過去式的思考:不斷檢討「我過去的產出服務了誰?我喜歡服務哪一群人?我喜歡做什麼事情又剛好是受眾也喜歡的?」。
2. 真實經驗:
AI 永遠無法取代真實經驗,你的真實經驗/感受也是和受眾建立情感連結最重要的內容,例如曼報的 Emo 片段是粉絲最愛的。
試著思考——你怎樣在你的創作內容中加上真實經驗?你怎樣讓這個真實經驗跟受眾產生共鳴,而不是生活廢文?(i.e. 你怎樣挑選真實經驗來支撐你的內容?)
3. 人脈網絡:
創作本質上是交朋友。我的人生從開始寫作之後有非常大的突破,全部都是因為寫作而認識了新的朋友,有新的工作機會。
好好交朋友,真心對待每一個認識的人,不要只想著利用誰,善待鄰舍如同自己。
4. 不要想著完美,想著真實。
如果你想要產出有趣的東西,就盡可能勇敢面對自己的不完美。我認為這個邏輯所有領域創作者通用。
完美很討人厭,不要試圖完美。
5. 不要純做文字,往 podcast 跟影片方向發展
至少聲音影片 AI 假不了(目前),而且影片與聲音會建立更強的情感連結。我也不會停留在純文字了,這個時候不做什麼時候做?
6. 元創作
如果你喜歡搞事,你想探索「新型態的創作者是什麼?」,那我觀察到的一個方向是:創作關於創作的創作。
例如過去我們可能是寫一本小說,但現在你是否可以把小說情節 Fine-Tune 成一個語言模型?
如果你把小說情節中的不同角色設定訓練成不同語言模型,讓他們自行對話,自行發展情節,那會怎麼樣?那會不會是每次情節都不一樣,連作者都不知道會怎樣發展的小說?
或者,如果你像我一樣寫一大堆筆記,你也可以訓練一個 LLM Twin 數位分身——然後跟它對話:是否有可能,你跟自己錄一集播客,看看你的第二大腦會怎樣把你嗆爆?
AI 不是取代創作,而是解放了新的創作型態:你可以創作關於創作的創作。
大概是這樣。很抱歉以上的建議都不是跟「賺錢」直接相關的。
上述的建議,都是可以讓你「特別、重要且難以取代」,如果可以做好這點,賺錢就真的只是副產品了。
延伸閱讀:英文老師寫出破億年收!這位台灣女婿的「觀點文」為何能吸引祖克柏、貝佐斯訂閱?
我用AI找資料,提升效率400%!拆解5大使用情境:怎麼問才能提升效率?
本文授權轉載自:周加恩facebook
責任編輯:黃若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