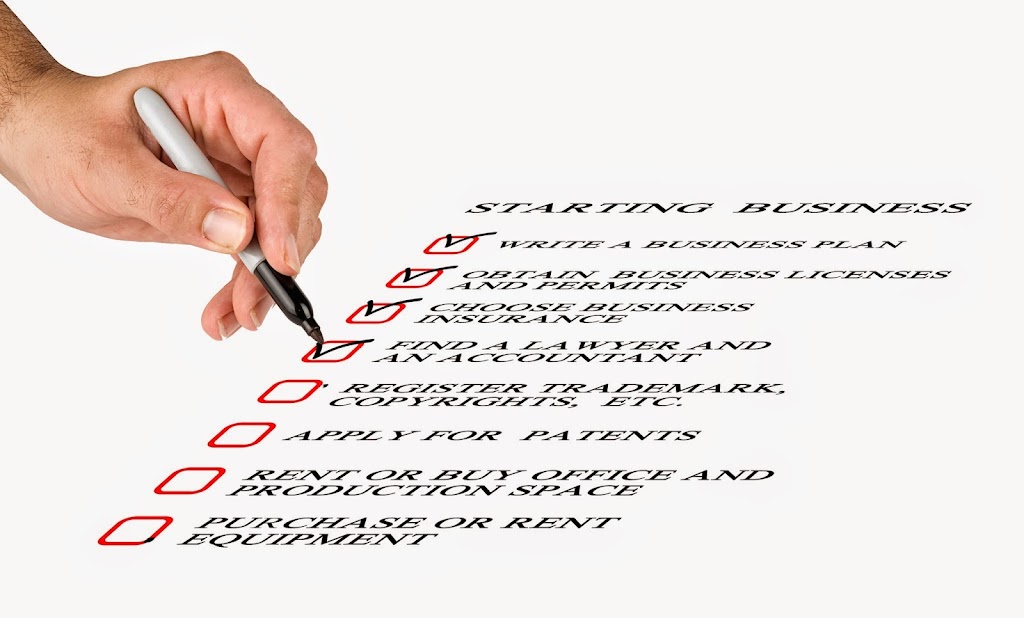當我們消費一項「產品」時,通常指的是我們用某個價錢,交換了一個機能,這機能幫你解決了生活中的一項難題;而當我們消費一種「服務」時,我們交換的,則是一種愉悅的感受。 那麼,當我們消費一齣「日劇」時,我們交換得來的,是什麼?之所以會有此問,乃是在9月份收看緯來日本台日劇《白色巨塔》,百感交集。
**一齣「高傳真」的時代劇
**
改編自1963年女作家山崎豊子同名小說,《白色巨塔》描述的是兩位同期同學醫生各自奮鬥人生的故事--唐澤壽明飾演的「財前五郎」自幼清寒,憑著努力以獎學金讀完醫學院,他相信唯有錘鍊更高的醫學技術才能出人頭地,擺脫社會對他的支配,進而支配別人。相對的,江口洋介飾演的「里見脩二」雖然和財前一樣,同樣奮力於醫學技術的研究,但他對權力遊戲卻有著「天真地不適應」,事實上,他不斷地在「醫生使命」和「醫界現實」徘徊掙扎(譬如:是把心力放在「好好照顧一位癌症末期病人」,還是「拯救更多有救患者的生命」之上?),這使他成為令所有「白色巨塔成員」頭痛的一號人物。兩位主角既惺惺相惜、又相互擷抗:財前主攻外科的食道癌,多次高難度手術讓他聲名遠播,里見則鑽研內科癌症基因療法,除了看病外,不時為末期癌症病患的安寧療護奔走。為了攀登權力的「白色巨塔」,財前五郎用盡各種鬥爭手腕、犧牲病患的感受,在對手的圍堵欺凌下殺出血路,但最終卻在權力顛峰之際罹患肺癌,死於里見的扶持之手;而里見則是生活於處處煎熬之中,一次次面對患者遺世的生離死別痛苦,為堅持難以言喻的天真,受盡醫院壓力和自我掙扎的折磨。在財前和里見的故事主軸外,鋪陳著對比的各個附屬的角色:由醫學部長、退職教授、醫局幕僚、醫學官僚組織構成的「醫療傳統」;由妻子、兒女、外遇愛人組成的「家庭系統」;以及因「資訊不對等」而被迫臣服於醫療權威下、代表「知識弱勢」的絕症患者。
表面上看,這是「弱者」反抗「強者」支配,千辛萬苦得勝的典型肥皂劇。但看了幾個片段後,就發覺整個製作團隊有更大的企圖--《白色巨塔》要訴諸的恐怕不是娛樂而已,它試圖透過各個「原型角色」經歷的戲劇糾葛,詰問著同樣身為工作者、同樣在職場之路披荊斬棘的觀眾,要他們自我解答那「認同」的焦慮:在當代社會裡,我是屬於「財前」那一種人,還是「里見」那一種?當我碰到誘惑或權力的欺壓時,我仍會認同權力嗎?如果不認同權力之路,就必須離開社會,但現代人誰又有這樣「陶淵明閉居南山之下」的悠然能力?也許作個含辛茹苦的妥協者是最保險的抉擇,但你又如何面對時時湧起的「本真良知」拷問和社會壓力?
**為何能拿下「收視率」第一?
**
上述的每一項難題,都是現代社會「上進者」的典型困境,財前、里見兩者都以推進醫學的知識和技術為使命,兩者都擁有極端的「個性」,各自和所處社會的「集體」主流價值對抗,但他們是知識的強者,才有這樣的幸運,世間平凡人毋寧更像是兩位主角的妻子、愛人、同僚、夥伴和病患,卑微地周旋在權力網絡中,能爭取到少許呼吸自由空氣的空間,就已經幸福異常。這也是為什麼最末集財前五郎的臨終場面,製作團隊會將它型塑成悲壯的「英雄化告別式」(heroic farewell),在全日本擷獲32.1%的近年最高收視率,讓數百萬個家庭為這個「負面主角」流下熱淚,因為大多數人都認可財前的「拚命向前」是每個人衷心的夢想,他高亢的權力欲望並非天生,而是來自社會壓力的不得不然,這使他採取了「奪權以反抗權力」的強悍心智,因而觀眾會認為財前比里見更接近「真實」,他是一位代表現實職場工作者們去拚搏的人,大多數人在戲劇的財前中,看到了真實世界中自己命運的幽微和苦澀,準確地說:觀眾是為自己滴下了眼淚。
對低迷的日本影劇產業而言,由去年10月演到今年春季的《白色巨塔》,可說是突破性的指標,從收視率來看,全部21集平均23.7%、最終集32.1%(關東32.1%、關西39.9%),都是近5年最佳成績;最值得一提的是,《白色巨塔》乃是近10年來唯一沒有「偶像」木村拓哉擔綱,而收視率仍能突破20%的日劇,也是近20年來,由「負面主角」、「沉重故事」而能取得收視率冠軍的唯一影集。
**日劇的世代交替
**
然而,《白色巨塔》能這麼吸引人,除了唐澤壽明、江口洋介、黑木瞳、西田敏行、伊武雅刀、矢田亞希子的卓越演技外,1958年出生的富士電視台製作統籌大多亮是個關鍵人物,正是他青年慧眼的感度,找來同為新世代的編劇、導演、音樂、攝影等工作團隊,革命性地改寫了日劇的製作水準。其中1961年出生的編劇井上由美子的改編功力,連台灣觀眾都覺耳目一新,除了許多深刻的對白(「人的慾望永無止境,但那不也是最純樸的東西嗎?」、「是醫生拯救病人,還是病人拯救醫生?」),《白色巨塔》能牢牢抓住觀眾視線,在於她技巧地塑造出價值光譜裡一組組二元對立的主角,誘引觀者來認同:財前與里見(代表「本真良知」的弱與強)、鵜飼醫學部長與東教授(代表「權力」的黑與白)、財前妻子與外遇愛人(代表「愛情」的真與假)、里見妻子與佐芝子(代表「弱者」的懷疑與定見),甚至訴訟裡的兩個律師,都是兩種社會典型(代表「職場」的專業主義與理想主義)的對峙。身為職場工作者的日劇觀眾,很容易在戲劇裡對照出自己的人生。
井上之外,兩位少壯導演西谷弘、河野圭太用對比視角來勾勒人物價值抉擇的焦慮、現代生活的掙扎,也是近年日劇拍攝傳統的大突破,舉例來說:第一集片頭,財前五郎閉目站立於窗前,哼著華格納〈唐懷瑟序曲〉,隨著上行和絃模擬食道癌手術的手部步驟,宛如交響樂團裡的指揮,這個將黑暗主角「聖化」的畫面組合,隨後再度於出現財前到華沙進行明星表演般的教學手術,那種沉醉於其中的光榮感,微妙呼應日本社會對「技術」的崇拜和「世界認同」的渴求,難怪動人。而如果你能對華格納多了解些,當知他的音樂當年深獲納粹醫生們喜愛,在於他的管絃樂作曲法有著特殊的集體性召喚,聽者很容易產生「獻身」的榮耀感,正因如此,戲中的華沙女接待引領財前醫師參觀二次大戰是斯威辛集中營(Oswiecim),讓財前於雪景中陷入良知和權力的糾葛,不禁令觀眾恍然大悟,原來整部劇集是如此「精密圖謀」,揉合了西方和東方的歷史隱喻,由第一集就已經設定好每個關鍵畫面和情緒點,日劇自此,已經走出木村拓哉立下的「青年時代」,而走入另一個「壯年時代」了。
**創新者的勇氣
**
雖然象徵醫院的「白色巨塔」裡黑暗遍布(每逢律師調閱資料,醫師總要拉下室內窗簾),但導演和劇作組在拍攝手術房和實驗室的器具和流程時,卻又營造出拯救人命的真摯科技美感,讓你對醫院抱持著愛恨交織的焦慮,我相信:正是如此不容易辨識出絕對善惡的「不確定性」(uncertainty),《白色巨塔》才如斯好看。
看完《白色巨塔》,偶而到網路上找資料,才發覺--其一:劇作組為了求真,請來日本食道癌和胃癌權威、93歲千葉大學名譽教授中山桓明,擔任唐澤壽明「手勢演出」的指導者,細心之至讓人驚訝。其二:《白色巨塔》拍攝時,大部分演員都重看1978年第二次搬上螢幕的舊作,因為當年原作者山崎豊子認為該齣劇中飾演「財前」的演員田宮二郎,最能代表她小說中的角色,而田宮二郎確實也因為真情投入,在最後集播出前以獵槍自殺,促成了當年31.4%的「收視率障礙」,全部演員和劇作組此次重拍《白色巨塔》,其實也是向他們心中的陰影挑戰。
在日劇《白色巨塔》之中和之外,你是見不到一個「無夢」的工作者的,這正是我百感交集的來源,在台灣同樣黑暗的社會劇場裡,如果少了一點一點每天要創新一點的螢光,就果真是漆黑一片了。